摘要以馬克思為界,哲學(xué)實(shí)現(xiàn)了主體革命。從古希臘到后現(xiàn)代的全部西方哲學(xué)都以人為研究對(duì)象,但馬克思之前的人是抽象精神,或是康德的理性,或是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中的上帝,無論是哲學(xué)還是宗教,都以抽象的觀念規(guī)訓(xùn)世界,規(guī)訓(xùn)人。馬克思之前的人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是人的神性。與此相反,在馬克思實(shí)現(xiàn)向唯物史觀轉(zhuǎn)換之后,“現(xiàn)實(shí)的人”成為馬克思的研究對(duì)象,或者說,馬克思唯物史觀正是奠基于“現(xiàn)實(shí)的人”基礎(chǔ)之上。主體的轉(zhuǎn)換帶來了馬克思真理觀的轉(zhuǎn)變,此后,真理不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現(xiàn)實(shí)的人”之生存。馬克思之后,全部哲學(xué)的研究不再主要研究人的神性,而是在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xué)的懸擱———直面事實(shí)啟發(fā)下,從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生存中發(fā)掘人,海德格爾的“此在的生存論分析”成為這一轉(zhuǎn)換的標(biāo)志性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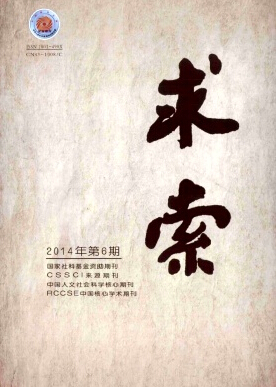
本文源自王清濤, 求索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7-17
關(guān)鍵詞認(rèn)識(shí)論斷裂;西方哲學(xué)的斷裂;主體革命
人始終是哲學(xué)研究的主題,然而馬克思之前,無論是哲學(xué)還是宗教,僅只研究抽象的精神,真正的人始終未能進(jìn)入哲學(xué)視野。馬克思以“現(xiàn)實(shí)的人”取代黑格爾的“自我意識(shí)”,實(shí)現(xiàn)了哲學(xué)主體的革命。馬克思哲學(xué)主體革命帶來了整個(gè)西方哲學(xué)主體的革命,以馬克思為界,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學(xué)不再以抽象的人作為哲學(xué)研究的主要對(duì)象,取而代之的是有生命的個(gè)人,海德格爾的“此在的生存論分析”成為這一轉(zhuǎn)換的標(biāo)志性命題。套用這一命題,尼采哲學(xué)是“此在的強(qiáng)力意志分析”,弗洛伊德哲學(xué)是“此在的精神分析”,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回歸生活世界”則是“此在的生活世界分析”。哲學(xué)從對(duì)“此在”的分析出發(fā),懸擱了托馬斯·阿奎那的人性維度,懸擱了先驗(yàn)主體,雖仍然是沿著人的解放之路狂奔,但所得到的結(jié)論,只能是人的本質(zhì)①。哲學(xué)主體從神圣維度中解放出來,人的生存世界也從天國(guó)返回到人間,當(dāng)人和世界不再為抽象的觀念所規(guī)訓(xùn),而是由“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生存自身所決定,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存在本身才是真理,真理觀革命將人從形而上學(xué)的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為真正的人類歷史開辟了道路。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序言》中講,人類的史前時(shí)期就以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終結(jié)而告終,“人類社會(huì)的史前時(shí)期就以這種社會(huì)形態(tài)而告終”①。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人類歷史,不但是指結(jié)束資產(chǎn)階級(jí)的統(tǒng)治,無產(chǎn)階級(jí)當(dāng)家作主,而且是指人不再由抽象的觀念所規(guī)定,是人的現(xiàn)實(shí)的生存決定自身。馬克思發(fā)現(xiàn),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規(guī)定人的不再是抽象觀念,而是資本的力量,對(duì)物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已經(jīng)取代了對(duì)上帝的信仰,資本邏輯取代了抽象觀念成為人和世界的決定力量。從這種非人性的力量對(duì)人的劫持中解放出來,就是讓人自己規(guī)定自己,這就是主體的轉(zhuǎn)換和人的解放,主體的轉(zhuǎn)換自身就是真理觀革命。
一、前馬克思的西方哲學(xué)之主體是精神
從古希臘開始,哲學(xué)就以人為對(duì)象。然而,無論是宗教還是哲學(xué),馬克思之前的人都是抽象的人。蘇格拉底在為掙脫自然哲學(xué),確立精神哲學(xué)地位的哲學(xué)革命中居功至偉,他將德爾菲神廟的箴言“認(rèn)識(shí)你自己”作為自己的哲學(xué)命題。哲學(xué)的功課就是要把握世界的規(guī)定性,這個(gè)規(guī)定性屬于世界,此即所謂的宇宙論哲學(xué)———這個(gè)規(guī)定性就是形而上學(xué)。由于世界的規(guī)定存在于自然之中,只有去拷問自然,才能把握這個(gè)世界的規(guī)定。自然的規(guī)定性不但主宰自然,而且主宰人世。但蘇格拉底提出“認(rèn)識(shí)你自己”,他的意思是說反求諸己就可以認(rèn)識(shí)世界的規(guī)定性。在自然哲學(xué)那里,任何一種規(guī)定性都屬自然本身所有,但蘇格拉底卻說人的認(rèn)知能力中存在著這樣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也就是說世界上的一切規(guī)定性都僅僅是因?yàn)槿说闹橇哂刑峁┻@種規(guī)定性的可能,是因?yàn)槿说恼J(rèn)知能力賦予了世界這種規(guī)定性。“允諾”是海德格爾的概念,即允許和承諾的意思,“允諾”這個(gè)概念可以很好地詮釋蘇格拉底的人與自然規(guī)定性之間的關(guān)系———是人的大腦“允諾”這個(gè)世界的規(guī)定性,不是世界天然具有這種規(guī)定性,這個(gè)規(guī)定性來自人的大腦,它不是對(duì)象世界自身所具有的,對(duì)象世界自身不存在這個(gè)規(guī)定性。人的大腦自身“允諾”了這個(gè)世界的規(guī)定性,就是人的大腦允許這種規(guī)定性的出現(xiàn)。 對(duì)此,趙敦華先生說,蘇格拉底“要求首先研究人自身,通過審視人自身的心靈的途徑研究自然。他認(rèn)為人的心靈內(nèi)部已經(jīng)包含著一些與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則,主張首先在心靈中尋找這些內(nèi)在原則,然后再依照這些原則規(guī)定外部世界。……必須求助于靈魂內(nèi)的原則去發(fā)現(xiàn)事物的真理。他說: ‘在任何情況下,我首先確定一個(gè)我認(rèn)為是最健全的原則,然后設(shè)定:凡是看起來符合這個(gè)原則的東西,不管是在原因方面,還是在其他方面相符合,都是真的;凡是與之不相符合的東西,就不是真的。’”②蘇格拉底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提出了“知識(shí)即美德”,他的意思是:世界的秩序本于人的精神法則,人的精神的秩序與世界的秩序相同一,世界的秩序即知識(shí),知識(shí)是人的心智的秩序的體現(xiàn),是美德的“定在”,所以“知識(shí)即美德”。蘇格拉底還常說,“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他要做“精神上的助產(chǎn)士,幫助別人產(chǎn)生他們自己的思想”。這跟蘇格拉底“認(rèn)識(shí)你自己”是完全一致的,因?yàn)槟阕约壕竦慕Y(jié)構(gòu)就是世界的秩序,所以認(rèn)識(shí)世界在于開啟心智。由此可見,蘇格拉底所謂的“認(rèn)識(shí)你自己”,并非認(rèn)識(shí)現(xiàn)實(shí)中生存的自己,而是精神自我。蘇格拉底將自己引向了精神自我,這成為西方哲學(xué)的基本原則,這一研究趨向被秉持2000年之久,直至馬克思,哲學(xué)中的人才從抽象精神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中的人。
笛卡爾為主體理性主義哲學(xué)奠基,其“我思”主體更是一個(gè)純粹的精神主體。笛卡爾之后,康德所提出的理性主體當(dāng)然也是純粹的精神主體,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人的認(rèn)識(shí)能力是純粹理性的能力,而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康德直接斷言人是“理性存在者”,就是說人是理性所規(guī)定的存在者,人不同于人之外的任何一個(gè)存在者,人是由理性規(guī)定的,人就是理性的定在,因而人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者,“這個(gè)存在者服從自己特有的,亦即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立的純粹實(shí)踐法則,因而人格作為屬于感官世界的,就其同時(shí)屬于理知世界而言,服從于他自己的人格性”①。對(duì)于“理性”是什么,康德已經(jīng)在《實(shí)踐理性批判》中予以揭示,康德的理性其實(shí)就是邏各斯,就是上帝,就是道。康德對(duì)自由的承諾根植于人的神性。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里面區(qū)分了物本身和經(jīng)驗(yàn)世界,認(rèn)為人只能把握經(jīng)驗(yàn)世界,不能把握物本身,人的認(rèn)識(shí)能力不能夠到達(dá)物本身。但是因?yàn)槿耸?一個(gè)理性存在者,理性規(guī)定著人的本性,這個(gè)由理性規(guī)定著的人就是物本身。物本身是自己決定自己的一個(gè)東西(亞里士多德的自因),人(物本身)由理性所規(guī)定,理性既是認(rèn)識(shí)主體也是存在本身, 二者是同一的。由于人僅僅受到自己的理性的規(guī)定,所以,人是一個(gè)自由者,如果人要受到人之外的東西所規(guī)定,那么人必然是不自由的,當(dāng)人僅僅是自身所理解的這個(gè)上帝(精神的,就是理性)的規(guī)定的時(shí)候,他是絕對(duì)自由的。康德的自由離開了自然必然性。他有兩套邏輯,第一套邏輯就是自然的因果性。自然因果性是指,在經(jīng)驗(yàn)世界里面人們打交道的一切物質(zhì)性對(duì)象,總處在物質(zhì)性對(duì)象前后相繼的鏈條中,任何一個(gè)對(duì)象它前面肯定有原因,所以說任何一個(gè)對(duì)象所體現(xiàn)出來的都是必然性,也就是說它是不自由的。但是在人這里,他前面沒有任何限制去規(guī)定他,人離開了經(jīng)驗(yàn)世界的因果序列,人是自身規(guī)定自身,所以說人是一個(gè)無條件的存在者,人離開了必然性成為一個(gè)自由存在。成為自由存在是人的一個(gè)位格,是人的“天位”。位格本是舞臺(tái)上的面具,在此可以理解為人的 一種生存狀態(tài)。康德肯定人的“天位”,他把人導(dǎo)向了神圣的位格,為人通往神圣存在開辟了道路, 打開了一扇門,康德哲學(xué)中的人是神圣之人,康德說:“道德法則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雖然夠不神圣了,但在他的人格之中的人性對(duì)他來說卻必須是神圣的。”②在康德看來,上帝是普遍的元始存在者,是實(shí)體存在的原因,也是理性存在者的原因,“一旦人們假定上帝作為普遍的元始存在者也是實(shí)體實(shí)存的原因(這是一個(gè)永遠(yuǎn)也不可以放棄的命題,除非把作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的上帝概念,連同在神學(xué)中一切東西都依賴的上帝之充足性一起放棄掉),人們就必須也承認(rèn),人的行動(dòng)在完全不受它們控制的東西中,亦即在一個(gè)與人不同的、人的存在及其因果性的全部規(guī)定所完全依賴的最高存在者的因果性中,有它們的規(guī)定根據(jù)”③。足見,康德的人性實(shí)乃神性。
黑格爾的人也是一個(gè)純粹精神,因而黑格爾哲學(xué)又被稱為精神哲學(xué)。在黑格爾看來,人高于自然界、高于動(dòng)物之處就在于,人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能夠“思考自己”即具有自我意識(shí)的精神實(shí)體,是一個(gè)能夠擺脫物質(zhì)、必然性的束縛而實(shí)行獨(dú)立自決的自由的精神實(shí)體。既然人是一個(gè)自由的精神實(shí)體, 因此人即精神、精神即人,馬克思講黑格爾的人其實(shí)是人的自我意識(shí),“人=自我意識(shí)”④。精神哲學(xué)的任務(wù)就是描述“絕對(duì)理念”通過自己的最高產(chǎn)物———人回復(fù)到自己、自己認(rèn)識(shí)自己,實(shí)現(xiàn)思維與存在同一的過程。黑格爾哲學(xué)正是對(duì)抽象概念的把握,因而黑格爾的人是精神,他在《宗教哲學(xué)講演錄》里講,人就是精神,精神就是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于他是思想,是具體的思想,更確切地說,人是精神”⑤。現(xiàn)實(shí)中生存的人不在黑格爾的研究范圍之內(nèi),他的哲學(xué)主體是精神,以精神取代人。由此可見,在西方哲學(xué)發(fā)展歷程中,從蘇格拉底直到黑格爾,中間雖然經(jīng)過一系列起承轉(zhuǎn)合的環(huán)節(jié),但他們研究的對(duì)象都是精神,并以精神取代人。這個(gè)精神是一般的精神,這個(gè)一般的精神是道,是邏各斯,是上帝,是絕對(duì)精神。馬克思之前的全部西方哲學(xué)視野中的人都是精神,是人的神性。
二、“認(rèn)識(shí)論斷裂”與哲學(xué)主體革命
馬克思“認(rèn)識(shí)論斷裂”———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和成熟時(shí)期馬克思的思想之間存在斷裂的論斷——— 是阿爾都塞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阿爾都塞重新闡述馬克思的前提,也是他之所以能“保衛(wèi)馬克思”的關(guān)鍵所在。阿爾都塞的馬克思“認(rèn)識(shí)論斷裂”是指,從1845年《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起,馬克思的哲學(xué)實(shí)現(xiàn)了從意識(shí)形態(tài)的前科學(xué)狀態(tài)轉(zhuǎn)變到獨(dú)創(chuàng)的科學(xué)體系中來,盡管晚期阿爾都塞對(duì)此有所反省,將 “認(rèn)識(shí)論斷裂”解釋為馬克思哲學(xué)發(fā)展過程自身的斷裂,而不是同外部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斷裂,但根本看來, 阿爾都塞從結(jié)構(gòu)主義立場(chǎng)上來審視馬克思哲學(xué),他離開了哲學(xué)的主體,從整體理解馬克思,認(rèn)為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吸取的不是辯證法和異化概念,而是“無主體過程”的哲學(xué)范疇,指出社會(huì)是由經(jīng)濟(jì)、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等因素按一定結(jié)構(gòu)方式構(gòu)成的復(fù)雜統(tǒng)一體,歷史發(fā)展不是按“人的本質(zhì)的異化”和“揚(yáng)棄異化”的人道主義方式進(jìn)行,而是由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構(gòu)成的“無主體過程”。但我們?cè)趯?duì)阿爾都塞 “認(rèn)識(shí)論斷裂”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馬克思的“斷裂”卻恰恰是哲學(xué)主體的轉(zhuǎn)換。1845年之后,不是馬克思哲學(xué)轉(zhuǎn)變?yōu)闊o主體的過程哲學(xué),而是馬克思擯棄了既往的神圣主體,以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生存作為自己哲學(xué)的根基,因而現(xiàn)實(shí)的人也自然成為馬克思哲學(xué)的主體與社會(huì)歷史主體。阿爾都塞事實(shí)上拋棄了哲學(xué)與社會(huì)歷史的中項(xiàng)———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環(huán)節(jié),以社會(huì)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取代現(xiàn)實(shí)的人,其可能帶來的后果是取消人的主體性。任何的經(jīng)濟(jì)、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等因素都不能離開其主體,在唯物史觀視域中,這一主體只能是現(xiàn)實(shí)的人。
阿爾都塞對(duì)馬克思哲學(xué)作了認(rèn)識(shí)論劃分,但從馬克思哲學(xué)自身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來看,馬克思哲學(xué)分期的根據(jù)卻是因?yàn)檎軐W(xué)主體由抽象到現(xiàn)實(shí)的轉(zhuǎn)向。1845年之后,馬克思哲學(xué)的主體由抽象的人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人。早在實(shí)現(xiàn)唯物史觀轉(zhuǎn)換之前,馬克思就經(jīng)常使用“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唯物史觀的樞紐性概念,然而,以1845年的《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為界,“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哲學(xué)中的含義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馬克思開始時(shí)所使用的“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概念是與舊哲學(xué)“抽象的人”相對(duì)立的現(xiàn)實(shí)的感性的人。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中就在使用“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概念,他提到“德國(guó)人那種置現(xiàn)實(shí)的人于不顧的關(guān)于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產(chǎn)生,也只是因?yàn)楝F(xiàn)代國(guó)家本身置現(xiàn)實(shí)的人于不顧,或者只憑虛構(gòu)的方式滿足整個(gè)的人”①。此處的“現(xiàn)實(shí)的人”是對(duì)德國(guó)哲學(xué)抽象主體的反動(dòng),是現(xiàn)實(shí)中生存的人。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同樣多次使用 “現(xiàn)實(shí)的人”概念,如他曾說,“所謂基督教國(guó)家只不過是非國(guó)家,因?yàn)橥ㄟ^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創(chuàng)作所實(shí)現(xiàn)的,并不是作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②。在此,馬克思的現(xiàn)實(shí)的人所凸顯的是與基督教的神圣的人相對(duì)立的人,基督教神圣的人是要建立神圣的天國(guó),其生存也是神圣的生存, 而現(xiàn)實(shí)的人不僅生活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而且建構(gòu)屬于人的生存世界。從這里可以看出,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是馬克思在《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完成的,是指通過自己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改造世界的活動(dòng)確證自身的人。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絕不臣服于生存必然性,絕不是一個(gè)必然性主體;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是自覺的自為存在,他自己設(shè)定自己,自己實(shí)現(xiàn)自己,自己確證自己。馬克思視野中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是無產(chǎn)階級(jí),無產(chǎn)階級(jí)解放自我的革命性實(shí)踐不僅確證自身,而且使無產(chǎn)階級(jí)的生存通往另一神圣維度,現(xiàn)實(shí)中的人是“現(xiàn)實(shí)的人”的一個(gè)位格狀態(tài),而無產(chǎn)階級(jí)則是“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全位格,是無產(chǎn)者的本己的生存,是無產(chǎn)者的“第三位格”。“第三位格”是“去成為”而不是 “被規(guī)定”,“去成為”是與永恒的絕對(duì)者的共在,與永恒的絕對(duì)者的共在開啟了無產(chǎn)階級(jí)事業(yè)的神圣維度。“去成為”是一種自我解放,而“被規(guī)定”則是被奴役。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在革命的實(shí)踐中確證自身的只能是無產(chǎn)階級(jí),唯心主義不可能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人”,舊唯物主義視野中的“現(xiàn)實(shí)的人”只是經(jīng)驗(yàn)的直觀的人。舊哲學(xué)不可能發(fā)現(xiàn)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當(dāng)然與唯物史觀無緣。
馬克思哲學(xué)主體的轉(zhuǎn)換與唯物史觀的創(chuàng)立是同一個(gè)過程。這個(gè)過程經(jīng)歷了幾個(gè)環(huán)節(jié),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已經(jīng)超越了黑格爾及其追隨者(鮑威爾等)的“自我意識(shí)”,指出“自我意識(shí)”是感性存在者的自我意識(shí),而不再是純粹抽象的自我意識(shí)。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馬克思進(jìn)一步將人定格為工人,工人的本質(zhì)還只是抽象的預(yù)設(shè)的人的本質(zhì)———自由自覺的勞動(dòng),但此時(shí)馬克思已經(jīng)看到了工人本質(zhì)在勞動(dòng)中的異化,更進(jìn)一步講,就是工人的本質(zhì)異化為勞動(dòng)產(chǎn)品,人的本質(zhì)第一 次以一種客觀的物質(zhì)性形式存在著,“首先,他將勞動(dòng)過程本身看作人的內(nèi)在本質(zhì)對(duì)象化的過程;其次,從勞動(dòng)、勞動(dòng)產(chǎn)品的審視中,人可以發(fā)現(xiàn)自己的內(nèi)在力量。也就是說,無論是勞動(dòng)活動(dòng)還是其最終產(chǎn)品,在其本質(zhì)上應(yīng)當(dāng)是勞動(dòng)的本質(zhì),是人的自由本質(zhì)的現(xiàn)實(shí)寫照。應(yīng)該說,沿著勞動(dòng)和勞動(dòng)產(chǎn)品是人的自由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的思路再向前走一步,就會(huì)得出人的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也是人的自由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形式,唯物史觀呼之欲出。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馬克思的人的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思維為其在《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最終實(shí)現(xiàn)向唯物史觀轉(zhuǎn)變準(zhǔn)備了條件,《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成為馬克思向唯物史觀躍升的最后一級(jí)臺(tái)階”①。在《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最終完成了對(duì) “現(xiàn)實(shí)的人”的構(gòu)筑,指出“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②。《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次確立了從客觀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確證人的本質(zhì)的唯物主義原理。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現(xiàn)實(shí)的人首先必須生存,而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生存的前提是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生存,“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gè)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gè)前提,這個(gè)前提是:人們?yōu)榱四軌?lsquo;創(chuàng)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gè)歷史活動(dòng)就是生產(chǎn)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chǎn)物質(zhì)生活本身”③。馬克思接著講, “已經(jīng)得到滿足的第一個(gè)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dòng)和已經(jīng)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chǎn)生是第一個(gè)歷史活動(dòng)”④。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馬克思揭示了“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內(nèi)在矛盾,并剖析“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內(nèi)在矛盾運(yùn)動(dòng)。馬克思哲學(xué)從“現(xiàn)實(shí)的人”的內(nèi)在矛盾運(yùn)動(dòng)的分析啟程,斷言:正是人的生存與實(shí)現(xiàn)的需要同社會(huì)存在之間的矛盾迫使人通過實(shí)踐活動(dòng)改變世界,并推動(dòng)社會(huì)歷史的運(yùn)動(dòng),而這一改造世界的革命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本身,正是現(xiàn)實(shí)的人的自我確證。由此看來,馬克思的主體是一個(gè)逐漸形成的過程,在真正“現(xiàn)實(shí)的人”這一歷史主體形成之際, 馬克思所實(shí)現(xiàn)的哲學(xué)革命也就看到了。
三、馬克思的主體革命與西方哲學(xué)的斷裂
馬克思的主體轉(zhuǎn)換促使了西方哲學(xué)的斷裂。馬克思之前與馬克思之后哲學(xué)的主體絕不是同一 個(gè)主體。馬克思之前觀念論占統(tǒng)治地位,人是抽象的人,是神圣的人,在馬克思之后哲學(xué)研究的人則是現(xiàn)實(shí)中生存的人,哲學(xué)告別了神圣主體,現(xiàn)實(shí)中人的生存成為哲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馬克思最終的價(jià)值目標(biāo)在于所有的人作為“人”獲得“根本且徹底的解放,亦即在現(xiàn)實(shí)的歷史運(yùn)動(dòng)中,通過對(duì)舊世界的改造和對(duì)私有財(cái)產(chǎn)的揚(yáng)棄而成為‘完整的人’”⑤。此后繼起的現(xiàn)象學(xué)———所謂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的懸擱,也正是懸擱了觀念論,懸擱了以神性來解釋的人性,以抽象代替現(xiàn)實(shí)。從此之后,哲學(xué)對(duì)人的研究不再是從超驗(yàn)的彼岸世界對(duì)人的研究,而是直面事實(shí)本身,是對(duì)此岸的生存中的人的研究, 并在這一研究中開出全新的哲學(xué)視界。
主體革命帶來了整個(gè)西方文明的動(dòng)蕩,胡塞爾恰恰生活在這樣一個(gè)不平靜的時(shí)代,傳統(tǒng)的歐洲現(xiàn)代文明處處危機(jī)四伏。表面看來其時(shí)的危機(jī)屬于科學(xué)危機(jī),是科學(xué)統(tǒng)治地位的動(dòng)搖,但本質(zhì)上這場(chǎng)危機(jī)卻是歐洲文明的危機(jī),是現(xiàn)代性的危機(jī)。主體革命帶來了新的價(jià)值觀的興起,這給一向穩(wěn)定的歐洲人的價(jià)值體系帶來了致命一擊,現(xiàn)代性一度失去了明確的方向,彷徨在無家可歸的路上。胡塞爾從物理學(xué)的客觀主義及其演變形式實(shí)證主義中發(fā)現(xiàn)了歐洲科學(xué)危機(jī)的根源,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yàn)槿藗冎匦聦ふ业揭粋€(gè)確定可靠的、普遍永恒的前提,并以此作為科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打開通向文明的大門。胡塞爾將其哲學(xué)轉(zhuǎn)向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胡塞爾后期現(xiàn)象學(xué)方法的根基。 胡塞爾后期現(xiàn)象學(xué)獨(dú)特的范式是先驗(yàn)還原的方法。胡塞爾后期現(xiàn)象學(xué)方法作為一種綜合思辨的哲學(xué)方法,為哲學(xué)研究開辟了廣闊的方法論視野,現(xiàn)象學(xu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為人類贏得了新的思想發(fā)展空間,能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jī)結(jié)合,為人類的思想危機(jī)提供了解決方法”①。
胡塞爾是20世紀(jì)的西方哲學(xué)家之一,現(xiàn)象學(xué)的奠基人。20世紀(jì)初,他發(fā)起的這場(chǎng)獨(dú)具特色的大規(guī)模的哲學(xué)運(yùn)動(dòng)———現(xiàn)象學(xué)運(yùn)動(dòng),終使現(xiàn)象學(xué)成為重要的哲學(xué)流派之一,之后的存在主義、語言哲學(xué)等哲學(xué)流派均從此得到啟發(fā)。以人本學(xué)為代表的現(xiàn)代哲學(xué)與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都繞不開現(xiàn)實(shí)中生存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神圣的人,它們告別了人的神性,而從人性中開啟哲學(xué)視界,海德格爾是重要推手。對(duì)“此在”的分析已經(jīng)成了海德格爾“烙有他自己名字的‘印記’因而可被直接辨認(rèn)出來的那些概念”②。海德格爾哲學(xué)基于對(duì)“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尼采哲學(xué)則是“此在的強(qiáng)力意志分析”,弗洛伊德哲學(xué)是“此在的精神分析”,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回歸生活世界”則是“此在的生活世界分析”。“此在”就是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生活的人,生活于此的,“在”就是把它自己敞開,“此在是這樣一種存在者:他在其存在中有所領(lǐng)會(huì)地對(duì)這一存在有所作為”③。在此,海德格爾的主體與康德之主體有驚人的相似,即二者都是為了開出自由而將人(理性、此在)理解為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自因的(亞里士多德在論述實(shí)體時(shí)講實(shí)體是自因的)。“此在”的分析就是對(duì)自己把自己敞開的這樣一個(gè)存在的分析。對(duì)這一存在的分析,是海德格爾哲學(xué)的功績(jī)。海德格爾的分析是此在的生存分析,人所遭遇的一切,包括時(shí)間、空間等全部形式都是在此在的生存分析當(dāng)中開顯的,什么是有意義的、什么是無意義的,都在這一分析當(dāng)中得到解釋。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哲學(xué)中,此在“向死而生”,他的生存論哲學(xué)以死為終結(jié)點(diǎn)來反思人的價(jià)值與生命的意義,于是,一切觀念都被重構(gòu)了。在這一重置的哲學(xué)語境中,人的生存世界中本來有意義的事情不再有意義,本來無意義的事情變得有意義,以這種方式的生存是本真的存在,反之就是人的沉淪,即非本真的存在,而海德格爾所期待的是本真的存在。 以死亡作為分析的支點(diǎn),人生的一切都被重新賦予了意義。與海德格爾相類似,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以及后現(xiàn)代哲學(xué)也都是對(duì)此在的分析,他們分別從對(duì)此在的生存分析中開出了自己的哲學(xué)。
對(duì)人的生活世界的關(guān)注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主題。后現(xiàn)代哲學(xué)中的反基礎(chǔ)主義、反理性主義、反本質(zhì)主義、反歷史主義、反本體論、視角主義、非中心化等思想緊密聯(lián)系、相輔相成,匯聚成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性的質(zhì)疑與批判、超越與解構(gòu)的根本特征。后現(xiàn)代哲學(xué)正是從對(duì)人的生活世界的分析中確立其哲學(xué)立場(chǎng)的,去中心化、多元化以及碎片化,反對(duì)形而上學(xué)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基本趨向,后現(xiàn)代哲學(xué)批判的終極目的就是“返回人的生活世界”。直接看來,現(xiàn)代性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標(biāo)靶,仿佛現(xiàn)代哲學(xué)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所指,但根本來講,馬克思主體轉(zhuǎn)換之后,全部哲學(xué),無論是現(xiàn)代哲學(xué)還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其批判與解構(gòu)的主旨,目標(biāo)都指向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同時(shí),也根本顛覆了傳統(tǒng)哲學(xué)與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神圣主體的建構(gòu)。
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與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回歸人的生活世界的潮流是馬克思開啟的,在21世紀(jì)來臨之際,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就開啟了回歸生活世界的征程。王南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是回歸生活世界的哲學(xué),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是一種實(shí)踐哲學(xué),實(shí)踐哲學(xué)與以往哲學(xué)的根本性區(qū)別也就是實(shí)踐哲學(xué)與理論哲學(xué)的區(qū)別,其根本之處在于如何看待人類生活中理論活動(dòng)與生活實(shí)踐的關(guān)系。“回歸生活世界意味著超越理論哲學(xué)理路,走向真正的實(shí)踐哲學(xué),意味著超越體系哲學(xué)而走向一種建立在諸主體對(duì)話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開放的、有限的體系,意味著一種基于理論與現(xiàn)實(shí)的對(duì)話關(guān)系的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歷史的批判”①。在明晰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是回歸人的生存哲學(xué)之后,整個(gè)中國(guó)哲學(xué)界有意識(shí)地將中國(guó)哲學(xué)逐漸拖離元理論的研究而轉(zhuǎn)向應(yīng)用哲學(xué)的研究,哲學(xué)研究日趨世俗化和向生活世界回歸。21世紀(jì)以來,政治哲學(xué)的勃興同樣是對(duì)哲學(xué)回歸生活世界的回應(yīng)。
四、主體的轉(zhuǎn)換與真理觀革命
主體的革命必然帶來真理觀革命。在馬克思完成哲學(xué)主體革命之前,觀念決定人,因而觀念是真理,真理以一種抽象的精神方式存在著,這種觀念的合理性取決于是否與對(duì)象相符合。但在馬克思完成哲學(xué)主體革命之后,主體不再取決于抽象的觀念,而是取決于人自身的生存———存在。根本來講,觀念論真理觀也是以存在為前提的,我們知道,觀念是純粹精神,而精神之所以是真理植根于精神本身即存在,巴門尼德講思維即存在,“因?yàn)樗季S與存在是同一的”②,精神不但就是存在,而且是比存在者更加真實(shí)的存在。然而馬克思發(fā)現(xiàn),將抽象的精神確定為真理會(huì)導(dǎo)致觀念對(duì)人的統(tǒng)治,從舊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是哲學(xué)的重要使命,而這一解放,根本來講是恢復(fù)存在(非精神形態(tài)的存在,而是意識(shí)意謂對(duì)象———存在者之存在)的真理地位,然而存在者之存在根本來講是非存在,因?yàn)榇嬖谡咧皇谴嬖谥?而沒有存在,存在者之存在是從人之生存中獲得的,這是海德格爾真理觀的基本主張,然而馬克思所強(qiáng)調(diào)的存在即真理乃特指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這一真理是決定一切存在(真理)的前提,人的存在是原始真理,就是說,人之存在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要服從人之存在,其存在在人之存在那里被重估,即人與奪其他存在者之真理。馬克思首先確立其全部哲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即人之生存,然后沿著人的生存離不開物質(zhì)生活資料這一唯物史觀線索對(duì)人的生存現(xiàn)象進(jìn)行揭示,并最終完成了對(duì)人的生存的組建。可以看出,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都以人的存在為原始真理,然而其分析方向則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是以“現(xiàn)實(shí)的人”的生存為出發(fā)點(diǎn),而海德格爾則沿著人的情緒揭示人的存在。馬克思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現(xiàn)實(shí)的真理。
馬克思實(shí)現(xiàn)主體革命后,主體由抽象觀念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人,觀念主體不需要吃、喝、穿、住,而現(xiàn)實(shí)主體首先要吃、喝、穿、住,世界就是在人的現(xiàn)實(shí)的生存———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被組建起來的,世界之存在服從于現(xiàn)實(shí)的人之生存———存在,于是馬克思實(shí)現(xiàn)了真理觀革命,即現(xiàn)實(shí)的人之存在決定世界之存在(真理),而不是觀念決定現(xiàn)實(shí)的人之存在,從而使人的解放道路躍上了一個(gè)新臺(tái)階。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