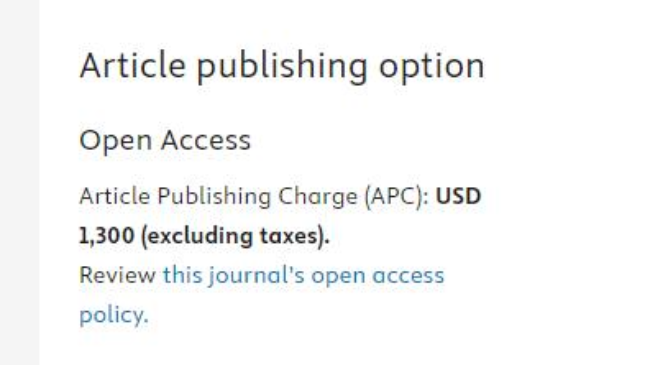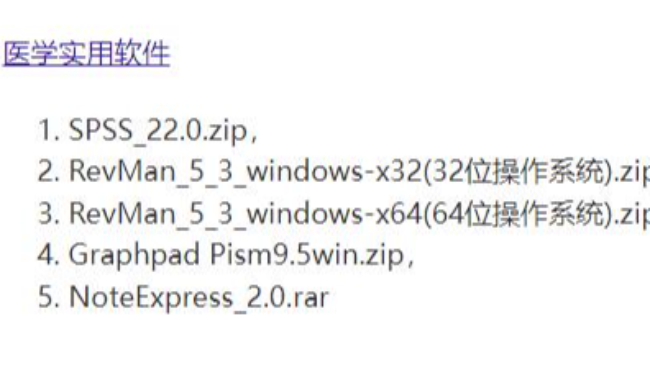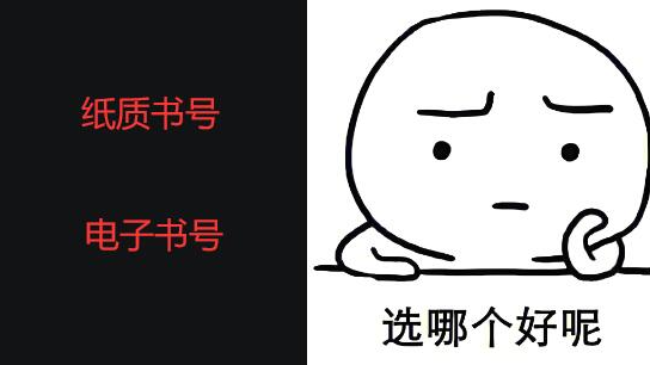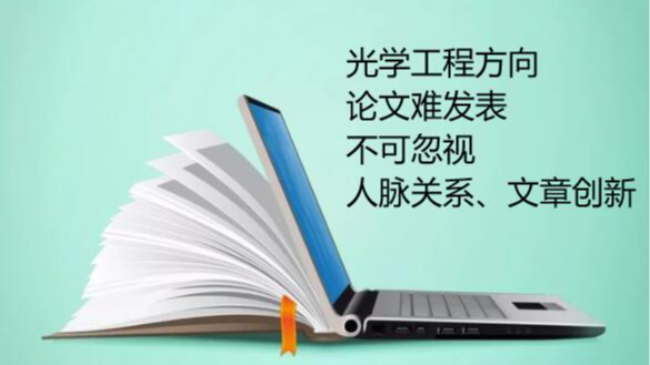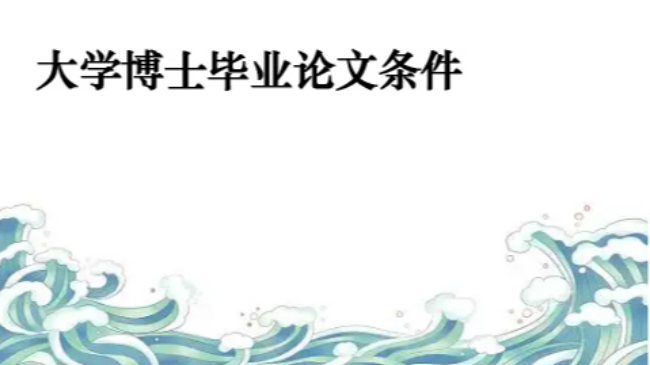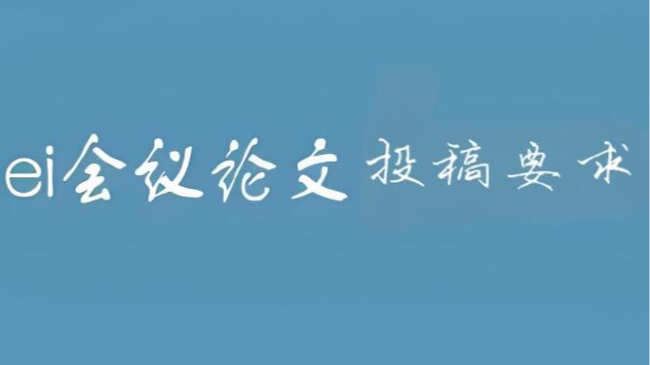文化消費(fèi)主義境遇下的當(dāng)代文學(xué)
一、文化消費(fèi)主義背景下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現(xiàn)狀
消費(fèi)主義作為文化意識形態(tài)話語,這種消費(fèi)主義的意識(文化)形態(tài)必然影響著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化方向,文學(xué)領(lǐng)域也不例外。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文學(xué)期刊。除了少數(shù)幾個(gè)文學(xué)刊物繼續(xù)原來的辦刊方針,堅(jiān)持原有的文學(xué)理念外,一部分純文學(xué)刊物無法繼續(xù)生存,如《漓江》、《昆侖》、《峨嵋》、《小說》均停刊;一部分向文學(xué)的邊緣拓展,完成純文學(xué)刊物向泛文學(xué)刊物或文化刊物的轉(zhuǎn)變。如《人民文學(xué)》、《作家》、《百花洲》對刊物重新定位,小說比重大幅縮減,廣義散文數(shù)量上升。其次,傳統(tǒng)審美理想與心靈凈化被人們漸漸拋棄,人們?nèi)找姘涯抗馔断蜃约旱腻X包和肉體,沉溺于淺顯的感官享受,那種對美好事物的虔敬之心和懷念情懷漸漸為浮躁之心和低俗之性所替代,贗品、東拼西湊的“大雜燴”、穿越劇、戲說歷史充斥于文化市場,人們對文化的膚淺與無深度變得日益習(xí)慣與沉溺其中,缺乏對人類靈魂的觸及與深層的關(guān)懷。消費(fèi)主義文化對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文學(xué)的深刻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一方面是文學(xué)外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變,激發(fā)文學(xué)生產(chǎn)機(jī)制的改變。在文化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文學(xué)生產(chǎn)傳播都受到市場機(jī)制的操縱,文學(xué)生產(chǎn)傳播從過去的宣傳機(jī)制、教育機(jī)制向利益機(jī)制轉(zhuǎn)變,在資本的運(yùn)作下,文學(xué)生產(chǎn)不再是個(gè)人生命體驗(yàn)和心靈感悟,而是在大工業(yè)原則操縱下的“簡單模仿”,正日益成為大批量組裝的“文化工業(yè)”。藝術(shù)生產(chǎn)者的獨(dú)創(chuàng)性漸漸式微了,不斷地重復(fù)一個(gè)話語:藝術(shù)不過是重復(fù)。而這種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化、重復(fù)化的最后結(jié)果就是:大眾的審美淺顯、物化,他們失去自己獨(dú)立思考的能力,成為庸俗、無風(fēng)格的大眾文學(xué)的犧牲品,只是依據(jù)大眾文化提供的模式指引自己的工作、興趣、好惡,成為無個(gè)性的具有消費(fèi)主義人格的人。另一方面是文學(xué)內(nèi)部從內(nèi)容到形式再到審美風(fēng)格的變化。文化消費(fèi)主義中,文學(xué)首先是作為一種精神消費(fèi)品而存在的,文學(xué)的“啟蒙”與“救亡”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的審美性功能被文學(xué)的消遣性、娛樂性功能所替代,文學(xué)書寫的內(nèi)容從以精神性追求為主轉(zhuǎn)向以物質(zhì)性滿足為主,文學(xué)的目的從以追求心靈提升為主轉(zhuǎn)向以張揚(yáng)欲望為主;文學(xué)人物從理性主體、德性主體轉(zhuǎn)變?yōu)橛黧w,文學(xué)傳統(tǒng)的宏大敘事被日常生活敘事、個(gè)人化敘事、欲望敘事替代。文學(xué)審美風(fēng)格雅俗對立的界限漸趨消弭,雅俗交融的審美風(fēng)格正在興起,特別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這一趨向,不僅是文學(xué)內(nèi)容的變化,同時(shí)也是文學(xué)審美風(fēng)格的轉(zhuǎn)型,深刻地參與了消費(fèi)主義文化塑造文學(xué)的過程。詹姆遜認(rèn)為消費(fèi)社會或后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打破了傳統(tǒng)藝術(shù)和生活的界限,藝術(shù)作為商品已經(jīng)成為普遍的文化景觀。第三方面,文學(xué)的功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由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生產(chǎn)的市場化與商業(yè)化的進(jìn)程逐日加深,再加上傳媒對文化消費(fèi)意識的大力倡導(dǎo),具有文化消費(fèi)主義人格群體的形成與擴(kuò)大,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失去精神趨向的人生觀、價(jià)值觀的逐漸勢強(qiáng),文學(xué)的功能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從原來的“揭露病態(tài),以求療救”的批判功能,悲天憫人、催人驚醒的社會職能變?yōu)閵蕵访癖姟埡箝e資的消遣職能。
二、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走向與擔(dān)當(dāng)
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后當(dāng)代文化的發(fā)展,折射著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文學(xué)生存的尷尬狀態(tài),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前途和發(fā)展前途迷茫。一方面?zhèn)鹘y(tǒng)文學(xué)媒介的力量在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被削弱,大眾傳媒成為文學(xué)的主宰者。文學(xué)被迅速傳播的同時(shí),文本個(gè)性和作者的獨(dú)創(chuàng)性也被大眾傳媒有意識地消解了。作者在獲得文化資本權(quán)利的同時(shí),他們的主體性也被扭曲了,在成名的同時(shí)也失去了自我。另一方面,文藝作品和文化產(chǎn)品變得淺表化和世俗化。整個(gè)文藝文化界發(fā)生了變化,消解歷史、消解意義、張揚(yáng)欲望、反對永恒、酷好當(dāng)下、棄置精神、奢談本能成為日漸宏大的聲音,人文精神、文學(xué)理想的聲音在氣勢宏大的消費(fèi)主義洪潮中漸漸式微。上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對享受欲、成名欲、權(quán)力欲、財(cái)富欲等欲望書寫隨處可見,表現(xiàn)為對物質(zhì)的奢華追求,文學(xué)對欲望的書寫層出不窮,花樣翻新;更廣泛、更典型的是對“物欲”和“情欲”的書寫,表現(xiàn)為對以性本能為主的感官享樂的追求;為了順應(yīng)消費(fèi)主義思潮和話語,文學(xué)創(chuàng)作漸漸迎合讀者的窺視欲和被培養(yǎng)出來的閱讀趣味。消費(fèi)浮華的外表下掩蓋不了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機(jī)。雖然資本將“八零后”、“九零后”文學(xué)運(yùn)作成一種時(shí)尚文化的潮流,在短短的時(shí)間內(nèi)成功地贏得了市場的追捧,但時(shí)尚總是遵循著前衛(wèi)-時(shí)髦-落伍的發(fā)展歷程,在時(shí)尚的同時(shí)也面臨著速朽的趨勢。消費(fèi)主義泛濫漸漸演變成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jī)。人們的信仰只體現(xiàn)在消費(fèi)與占有上,人性淪落于物性,“消費(fèi)拜物教”的觀念盛行,人與物之使用關(guān)系被異化,價(jià)值理念與精神世界被嚴(yán)重扭曲,人們常常在喧囂與浮華過后更加深切地體味到精神的匱乏、空虛無聊、生活無意義。同時(shí),文化的過度消費(fèi)與機(jī)械復(fù)制,造成文化壓抑了人自身對創(chuàng)造性的渴望及對體現(xiàn)自身能動(dòng)性發(fā)展的追求。文化消費(fèi)主義把物質(zhì)消費(fèi)作為衡量人的唯一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自我價(jià)值只表現(xiàn)于自我的消費(fèi)與享受之中,否定人的精神向度的多元性,人們生存取向的多維性變成單一的占有與消耗,人們漸漸厭惡這種文化工業(yè)的消費(fèi)方式。更為憂慮的是文化消費(fèi)主義的心態(tài)對青少年的成長和健康產(chǎn)生不良影響。青少年過度被“快餐文化”、“輕松肥皂劇”的熱鬧形式所吸引,而對人生和世界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深刻的認(rèn)知,嚴(yán)重地犯了膚淺和幼稚的弊病。文學(xué)評論界在這樣的文化境遇中必須要有所擔(dān)當(dāng)和作為,文學(xué)的命運(yùn)決不取決于物質(zhì)財(cái)富的多少,或是媒介對大眾話語權(quán)的閹割,只要人類情感生活依然存在,人們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還未喪失,文學(xué)就不可能永遠(yuǎn)消沉下去。一方面,作為一個(gè)有責(zé)任感的文學(xué)工作者,要找出一條既符合時(shí)發(fā)表展潮流,同時(shí)又能發(fā)揮文學(xué)的預(yù)見性、引導(dǎo)性、思想啟蒙性作用的文學(xué)發(fā)展新思路。面對世紀(jì)轉(zhuǎn)型期的社會審美趨向,首先應(yīng)考察當(dāng)今人們的真實(shí)思想狀態(tài)和心理欲求,關(guān)注社會、關(guān)注歷史、關(guān)注人類的心靈與情感,這是人文知識分子尤其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理論者所應(yīng)承擔(dān)起的一種崇高的文化責(zé)任。同時(shí)文藝工作者應(yīng)堅(jiān)守文學(xué)基本的審美立場,培育新的美育理念,提升人們的審美趣味,促使社會審美意識從淺俗向高雅轉(zhuǎn)型,并有意識地建造一種審美價(jià)值評價(jià)尺度,并促使人們自覺地利用這一尺度去判斷文學(xué)寫作行為,去影響人們文學(xué)審美與接受行為。與此同時(shí)需要引導(dǎo)人們樹立正確的文化消費(fèi)意識,提高人們的文學(xué)欣賞能力,自覺抵制和批判文化品位不高的文化作品成為人們主動(dòng)的訴求。另一方面,要充分發(fā)揮文學(xué)作品的思想戰(zhàn)斗堡壘作用。真正寫出能反映時(shí)代變遷、國計(jì)民生和百姓酸甜冷暖的雅俗共賞的好作品。文學(xué)的健康發(fā)展離不開一大批真正為大眾寫作,有使命感和責(zé)任感的作家,要增強(qiáng)作家的社會責(zé)任感,鼓勵(lì)作家沉靜心態(tài),深入生活,用好的作品來感染人、激勵(lì)人、鼓舞人,吸引人們的視野,滿足他們的心理訴求,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審美情趣,矯正人們的行為藝術(shù)。如畢飛宇的小說《推拿》、嚴(yán)玲鷗的《小姨多鶴》因貼近生活,挖掘文學(xué)作品的本質(zhì)、內(nèi)涵,在社會反響頗大,獲得好評。讓那些淺顯、低俗的文藝作品失去讀者與觀眾。
三、小結(jié)
綜上所述,在日漸膨脹的文化消費(fèi)主義大潮中,無個(gè)性模仿、大批量生產(chǎn)、主題的驚人一致性、思維方式的重復(fù)性這種支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邏輯原則,無助于提升人們的精神思想水平,無益于培養(yǎng)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個(gè)性化的受眾,長此以往,它對一個(gè)民族與國家的發(fā)展將產(chǎn)生可怕的顛覆的精神頹廢力量,必須引起我們文藝工作者的高度警醒,遏制這種局面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一方面需要作家的社會責(zé)任感;另一方面則需要審美理論家積極行動(dòng)起來,更有效地建構(gòu)符合當(dāng)代文化環(huán)境實(shí)際的、易于人們接受和領(lǐng)悟的文學(xué)理論話語和美學(xué)原則,這對作家和審美理論家都是一個(gè)嚴(yán)峻而有意義的挑戰(zhàn)。
作者:胡玉潔 單位:漯河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本文html鏈接: http://www.deadrain.cn/qkh/358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