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的元功能思想具有跨語言普適性,然而,不同語言對(duì)元功能有著不同的編碼方式。從及物性與邏輯 語義角度看,較之英語,漢語小句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更顯松散,邏輯語義關(guān)系具有不確定性; 相對(duì)于英語的語法自足性,漢語語法解釋多依賴于語境。從語氣角度看,英語通過限定化與指稱化編碼語氣結(jié)構(gòu),多數(shù)情況下漢語不需要類似語法手段,而是以直接融入語境的方式賦予小句人際潛勢(shì)。從主述位角度看,英語主位與述位的劃分較為明確,而漢語主位往往需要通過上下文來確定。不同的編碼方式表明,兩種語言的本質(zhì)差異在于: 英語為弱語境型語言,漢語為強(qiáng)語境型語言。在哲學(xué)思維層面,英語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 漢語主張?zhí)烊撕弦弧⒅骺鸵惑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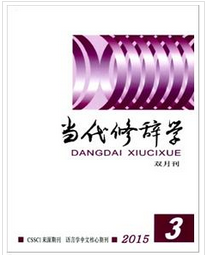
何偉; 仲偉, 當(dāng)代修辭學(xué)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9-18
關(guān)鍵詞 元功能 編碼方式 英漢語本質(zhì)差異 弱語境 強(qiáng)語境
一、引 言
元功能思想是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的理論基石,是對(duì)人類語言功能的高度抽象與概括。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認(rèn)為,語言有三大元功能: 概念功能、人際功能與語篇功能。其中,概念功能分為經(jīng)驗(yàn)功能與邏輯功能。三大元功能通過不同的語言資源體現(xiàn): 概念功能主要通過及物性系統(tǒng)、邏輯關(guān)系系統(tǒng)等體現(xiàn),人際功能主要通過語氣系統(tǒng)等體現(xiàn),語篇功能主要通過主位系統(tǒng)等體現(xiàn)。元功能思想具有普適性,可以講任何自然語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語言的編碼方式確有不同。因此,以元功能為切入點(diǎn)對(duì)比英漢語言,能洞悉兩種語言的本質(zhì)差異。
在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框架內(nèi),小句是三大元功能最核心的語法單位載體,該觀點(diǎn)與漢語學(xué)界的小句中樞說相通( 何偉、王敏辰 2018) 。具體而言,小句在認(rèn)知層面,表達(dá)一個(gè)事件( event) ; 在語義層面,表征一個(gè)情形( situation) ; 在形式層面,系體現(xiàn)多種意義的單一結(jié)構(gòu)體。從自上而下角度,小句的結(jié)構(gòu)成分及成分的組合與分布由意義驅(qū)動(dòng); 從自下而上角度,小句是體現(xiàn)意義的核心語法單位。針對(duì)小句這個(gè)重要的語法單位,本文主要通過對(duì)比英漢及物性結(jié)構(gòu)以及 邏輯 語義連結(jié)、語氣結(jié)構(gòu)、主述位結(jié)構(gòu)等三大元功能的編碼方式,呈現(xiàn)兩種語言在類型上的本質(zhì)差異,并在哲學(xué)思維層面對(duì)類型差異進(jìn)行闡釋。
二、英漢及物性結(jié)構(gòu)及編碼方式
人們對(duì)外部和內(nèi)心世界的體驗(yàn)主要通過及物性來表征,這是語言的經(jīng)驗(yàn)功能。盡管不同學(xué)者對(duì)及物性類型的劃分不盡一致,如 Halliday ( 1994) 、Martin et al.( 2010) 、何偉等( 2017a, 2017b) ,然而他們對(duì)小句及物性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的描述基本相同,均認(rèn)為及物性結(jié)構(gòu)包括過程、參與者與環(huán)境角色成分。其中,過程是核心成分,參與者一般是不可或缺成分,環(huán)境角色比較自由。Fawcett( 2000) 、何偉等( 2017a,2017b) 指出及物性結(jié)構(gòu)中的過程、參與者、環(huán)境角色分別對(duì)應(yīng)于小句中的主要?jiǎng)釉~( 英語) /謂體( 漢語) 、主語與補(bǔ)語、狀語。就編碼方式而言,英漢小句過程與參與者的潛勢(shì)填充成分表現(xiàn)出較大的差異( 何偉、王敏辰 2019) ,如下表所示:
英語小句表征的過程在形式上通常由動(dòng)詞說明,而漢語不僅可以由動(dòng)詞說明,還可以由名詞詞組、性質(zhì)詞組、數(shù)量詞組填充,或是由小句填充,構(gòu)成主謂謂語句。比如: ( 1) He adores Mama,and she him ①. ( 2) 常女士北平人,年十六歲,體態(tài)健美,歌喉嘹亮,性情尤為活潑天真。 ( 3) 河里的魚很多。 ( 4) 她臉色蒼白。例( 1) 兩個(gè)并列小句的過程均由動(dòng)詞說明,只是第二個(gè)小句中的動(dòng)詞承前省略。例( 2) 和例( 3) 中的“北平人”“十六歲”是名詞詞組,“健美”“嘹亮”“尤為活潑天真”是性質(zhì)詞組,“很多”是數(shù)量詞組,均填充小句的謂體。例( 4) 的謂體由小句“臉色蒼白”填充,而性質(zhì)詞組“蒼白”又做嵌入小句“臉色蒼白”的謂體。同時(shí),例( 2) 被認(rèn)為是流水句,含五個(gè)小句,后四個(gè)小句均承前省略主語“常女士”( 王文斌、趙朝勇 2017: 39) ,即如例( 4) 一樣,該例中的后四個(gè)小句均可視為主謂謂語句。此處的分析表明,例( 2) 至例( 4) 中的小句不存在動(dòng)詞“是”或“有”的省略情況,正如趙元任( 1968,1979: 56) 所說,漢語研究中“盡量少說省了字的原則”,因?yàn)檠a(bǔ)出的“省略”不止一種,而且也常常補(bǔ)不出。
如表 1 及上述分析所示,英語小句中的過程與參與者之間、不同參與者之間,都有較明顯的區(qū)分。英語過程由動(dòng)詞說明; 英語主語參與者由名詞詞組或小句填充,極少情況下由介詞短語填充( 如 On Sunday suits her) ; 補(bǔ)語由小句、名詞詞組、性質(zhì)詞組、數(shù)量詞組或介詞短語填充。與英語有所不同,漢語小句中的過程填充形式多樣; 漢語小句中做主語與補(bǔ)語的參與者有著相同的潛勢(shì)結(jié)構(gòu),都可由小句、性質(zhì)詞組、數(shù)量詞組、名詞詞組或介詞短語填充。漢語小句的參與者與過程也有著相似的潛勢(shì)填充單位,沒有特別明確的區(qū)分②。漢語小句中的過程與參與者在體現(xiàn)形式及編碼方式上的模糊性,使得小句在句法分析中具有不確定性。比如:
呂叔湘( 1979: 29) 認(rèn)為漢語句子作為一個(gè)動(dòng)態(tài)語法單位,在形式上可由一個(gè)主謂結(jié)構(gòu)、獨(dú)立動(dòng)詞或名詞詞組充當(dāng)。漢語句子與詞組的構(gòu)造原則基本一致,詞組加上語調(diào)可以獨(dú)立成句 ( 朱德熙 1985: 78) 。當(dāng)然,詞組與小句有內(nèi)在的區(qū)別,從系統(tǒng)功能視角來看,名詞詞組“一個(gè)腳印”之所以被視為一個(gè)小句,是因?yàn)樗谡Z義上表征的是一個(gè)情形,在認(rèn)知層面表達(dá)的是一個(gè)事件概念。英語中,這類小句被視為省略句,不論“一個(gè)腳印”被看作主語或補(bǔ)語( 如 A footprint is here /There is a footprint /I found a footprint here) ,小句均省略了表達(dá)過程意義的動(dòng)詞及其他參與者成分。漢語中,名詞詞組既可以做主語、補(bǔ)語,也可做謂體,可以說“一個(gè)腳印在某處”“某處有一個(gè)腳印”或者“某處一個(gè)腳印”。此處能補(bǔ)出的省略形式有多種,這也就違背了漢語研究中盡量少說省字的原則,正如呂叔湘( 1979: 67) 所說: “關(guān)于省略,從前有些語法學(xué)家喜歡從邏輯命題出發(fā)講句子結(jié)構(gòu),不免濫用‘省略’說。”
不僅如此,在語義層面,與英語相比,漢語所謂結(jié)構(gòu)形式完整的小句,語義結(jié)構(gòu)顯得松散得多。比如: ( 6) The book has been very heavily attacked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 7) His mother died at 56. ( 8) 信寫好了。 ( 9) 阿泰茲的書出版了。 ( 10) 新來的同志都已經(jīng)分配了工作。(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 ( 11) 王冕死了父親。( 鄧仁華《“王冕死了父親”的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闡釋》) ( 12) 非典時(shí)小李也病了一個(gè)妹妹。( 劉探宙《一元非作格動(dòng)詞帶賓語現(xiàn)象》) ( 13) 他們辦公室接連感冒了三四個(gè)人。( 劉探宙《一元非作格動(dòng)詞帶賓語現(xiàn)象》) ( 14) 趙云找了王鳳卿,馬岱找了程繼仙。( 張伯江《現(xiàn)代漢語的非論元性句法成分》) ( 15) 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這樣大。( 張伯江《現(xiàn)代漢語的非論元性句法成分》) 例( 6) 中,The book 在小句語義配置中系“受事”,在句法中做主語,以被動(dòng)語態(tài)形式出現(xiàn)。例 ( 7) 中,died 系不及物動(dòng)詞,His mother 作為“受事”,是不可或缺的語義成分。例( 6) 與例( 7) 兩個(gè)小句受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的制約,有主動(dòng)和被動(dòng)語態(tài)的區(qū)分,同時(shí)不及物動(dòng)詞只帶一個(gè)參與者成分,是英語中的語法常態(tài)。
例( 8) 至例( 10) 中的“信”“阿泰茲的書”“新來的同志”,語義上分別屬于“受事”“受事” 和“受事—擁有者”,都做小句的主語。英語中這些成分通常做補(bǔ)語,做主語時(shí)要用被動(dòng)形式。 “漢語只有被字句,沒有被動(dòng)句”( 沈家煊 2018: 7) ,這種體現(xiàn)形式是漢語的常態(tài),不是特殊情況。例( 11) 至例( 13) 中的“死”“病”“感冒”表達(dá)的過程,在英語中只能攜帶一個(gè)參與者,但在漢語中可同時(shí)帶有主語和補(bǔ)語,即有兩個(gè)參與者,分別是“受影響者—載體”和“受影響者—被擁有者”,小句的過程類型也不是這類動(dòng)詞通常所體現(xiàn)的典型動(dòng)作過程,而是“屬有型關(guān)系過程”( 鄧仁華 2018: 188) 。可以說,漢語中動(dòng)詞的及物與不及物的區(qū)分界限不明顯( 呂叔湘 1979: 40) ,或者說這種區(qū)分是不重要的( 沈家煊 2018: 6) 。例( 14) 中的兩個(gè)小句也不是動(dòng)作過程。在具體語境中,“趙云”“馬岱”都是戲劇角色,不是施事,“王鳳卿”“程繼仙”是扮演戲劇角色的演員,也不是單純的受事。例( 15) 動(dòng)作過程小句中,“致秋”不是施事。根據(jù)語境得知,致秋已經(jīng)過世,照片指的是她的遺像。可以看出,漢語的句法結(jié)構(gòu)與語義結(jié)構(gòu)不對(duì)等,“不同性質(zhì)的語法成分、不同角色的語義成分,可以進(jìn)入相同的句法結(jié)構(gòu)里遵從相同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 ( 張伯江 2011: 5) 。張伯江( 2018) 用大量的語言事實(shí)說明以動(dòng)詞為謂體的小句,主語與補(bǔ)語位置上的參與者角色與謂體的關(guān)系極其松散; 趙元任( 1968,1979: 45) 認(rèn)為: “關(guān)系松散到了如果放在別的語言里將成為不合語法的程度。”
三、英漢邏輯 語義連結(jié)及編碼方式
從邏輯功能角度來看,不論是形式層還是語義層,英語似乎比漢語體現(xiàn)出更強(qiáng)的邏輯性。何偉、劉佳歡( 2019) 通過語料庫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對(duì)比了英漢小句的邏輯語義關(guān)系及表征方式。結(jié)果表明,在表征方式上,英語小句之間多用邏輯標(biāo)記詞體現(xiàn)邏輯關(guān)系,而漢語小句之間則少有邏輯標(biāo)記詞出現(xiàn); 在邏輯配列及邏輯 語義關(guān)系上,英語多主從及增強(qiáng)類關(guān)系,而漢語多并列及延展類關(guān)系。比如:
( 16) No goals were scored,though it was an exciting game.球賽很精彩,可一個(gè)球也沒進(jìn)。( 潘文國(guó)《漢英語對(duì)比綱要》) ( 17) Mr A teaches physics,while Mr B teaches Chemistry. A 教師教物理,B 教師教化學(xué)。( 潘文國(guó)《漢英語對(duì)比綱要》) 例( 16) 與例( 17) 中,英語例句分別出現(xiàn)了邏輯標(biāo)記詞 though 與 while,分別表達(dá)主從轉(zhuǎn)折類增強(qiáng)關(guān)系與主從對(duì)比類增強(qiáng)關(guān)系。例( 16) 漢語例句中,“可”作為邏輯標(biāo)記詞表達(dá)并列而非主從轉(zhuǎn)折類增強(qiáng)關(guān)系。例( 17) 漢語例句中沒有出現(xiàn)邏輯標(biāo)記詞,兩個(gè)小句通過無標(biāo)記并置方式構(gòu)成并列關(guān)系———并置本身就是小句間的一種銜接手段( 姜望琪 2005: 37) ,但由于沒有使用邏輯標(biāo)記詞,邏輯 語義關(guān)系具有模糊性,可以理解為增強(qiáng)關(guān)系,也可以理解為延展關(guān)系。
通過對(duì)比英漢小句邏輯配列及邏輯 語義連結(jié)的編碼方式,可以看出,英語比漢語似乎體現(xiàn)出較強(qiáng)的清晰度與邏輯性。事實(shí)上,在具體言語行為中,上述例句對(duì)于漢語母語者而言是正常的表達(dá),是清晰的、符合邏輯的。對(duì)此,較為普遍的認(rèn)識(shí)與解釋是英語重形合,是一種理性思維; 漢語重意合,是悟性思維( 潘文國(guó) 1997) 。形合與意合是語法特征的概括,不能用來解釋語言之間的區(qū)別,反之,是一種循環(huán)論證。
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認(rèn)為,語言具有層級(jí)性,包括音系/字系層、詞匯 語法層、語義層或形式層 ( 包括音系/字系層和詞匯 語法層) 與意義層,語言系統(tǒng)之外為語境層。各個(gè)層級(jí)之間是體現(xiàn)關(guān)系,詞匯 語法層由音系/字系層體現(xiàn),語義層由詞匯 語法層體現(xiàn),語境層由語義層體現(xiàn)。其中,詞匯 語法層與語義層是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語言編碼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徑,在語義層構(gòu)建一個(gè)意義系統(tǒng)網(wǎng)絡(luò),在詞匯 語法層對(duì)意義特征選擇結(jié)果進(jìn)行編碼。在具體的語言識(shí)解中,又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徑。通過上述英漢對(duì)比,可以看出,兩種語言在詞匯 語法層有不同的編碼方式,這表明在語義層它們也有著不同的意義特征選擇。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認(rèn)為,小句間的邏輯 語義關(guān)系分為擴(kuò)展與投射兩大類,擴(kuò)展關(guān)系可細(xì)化為闡述、延展與增強(qiáng)關(guān)系,增強(qiáng)關(guān)系又可進(jìn)一步分為時(shí)間、地點(diǎn)、條件、原因、結(jié)果、轉(zhuǎn)折、對(duì)比等具體類別。例( 17) 英語小句中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詞 while 表明,在邏輯 語義關(guān)系系統(tǒng)中,該小句選擇的是對(duì)比增強(qiáng)關(guān)系; 漢語小句沒有邏輯關(guān)聯(lián)詞,邏輯 語義關(guān)系既可理解為對(duì)比增強(qiáng)關(guān)系,也可理解為轉(zhuǎn)折增強(qiáng)或是延展關(guān)系,也就是說,邏輯 語義的確定需要上下文語篇知識(shí),需要激活更大的意義網(wǎng)絡(luò)及更多的語境信息。
沈家煊( 2014: 1) 認(rèn)為漢語的運(yùn)作遵循“劉別謙定理”,“給出二加二,讓觀眾自己去得到等于四的答案”,如例( 17) 漢語小句沒有使用顯性邏輯關(guān)聯(lián)詞,小句簡(jiǎn)單地并置在一起,小句之間的邏輯 語義關(guān)系需要依靠語境來判斷。Matthews( 1981: 223) 指出,并置關(guān)系是最根本的語法關(guān)系,其他語法關(guān)系衍生于并置關(guān)系。可以說,并置關(guān)系是每種語法關(guān)系的深層關(guān)系。然而,與主謂、定中等語法關(guān)系不同的是,學(xué)界通常認(rèn)為并置關(guān)系屬于語用范疇( 姜望琪 2005: 37) 。Halliday 認(rèn)為在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外不需要語用學(xué)這一術(shù)語,“語用學(xué)似乎只是語篇語義學(xué)的另一個(gè)名稱”( Thibault 1987: 611) 。換句話說,語用學(xué)是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的應(yīng)有之義,存在于語言的語義層與語境層,或是語義層與詞匯 語法層之間的界面層。也就是說,對(duì)并置關(guān)系的解釋,要更多地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通過各層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來闡明。
即使是主謂關(guān)系,對(duì)于漢語而言,參照英語的形式邏輯來解釋也往往行不通。趙元任 ( 1968,1979: 41-44) 認(rèn)為,漢語主語與謂語( 謂體) 之間可以加上“啊”“吶”“嚜”“吧”等形式標(biāo)記,這樣漢語的一個(gè)整句就分成兩個(gè)零句,即不包含完整主謂結(jié)構(gòu)的小句,而且兩個(gè)零句都可以獨(dú)立。從這個(gè)角度看,漢語小句結(jié)構(gòu)可理解為一種簡(jiǎn)單并置關(guān)系,漢語似乎是以并置關(guān)系為主( 張伯江 2018: 454) 。也就是說,對(duì)漢語小句語法關(guān)系的識(shí)解要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語義語境為漢語語法研究的應(yīng)有之義,應(yīng)首先考慮。
四、英漢語氣結(jié)構(gòu)及編碼方式
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強(qiáng)調(diào)“語言產(chǎn)生于人類個(gè)體與他人進(jìn)行意義交流的經(jīng)歷”( Halliday 1978, 2001: 1) 。這意味著語言具有另一種元功能,即人際功能。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認(rèn)為,人際的本質(zhì)是交往,交往時(shí)語言編碼雙方進(jìn)入會(huì)話語境機(jī)制。交往的核心是給予與索取,英語主要通過語氣系統(tǒng)表征會(huì)話雙方的給予與索取角色。語氣( Mood) 主要由限定成分和主語組成。限定成分的功能在于使命題成為可爭(zhēng)議的目標(biāo)(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144) ,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是給予命題一個(gè)以說話人話語時(shí)間為基準(zhǔn)的參照點(diǎn),即賦予命題指示時(shí)間意義,從而在交流中為表征的過程進(jìn)行時(shí)間定位; 二是將說話人的判斷和態(tài)度加入命題,使命題處于“肯定”與 “否定”兩極之間,即給予命題以情態(tài)意義,從而使命題具有爭(zhēng)議性。這兩種資源的編碼方式在英語中已經(jīng)語法化,指示時(shí)間意義主要通過時(shí)態(tài)體現(xiàn),情態(tài)意義主要通過情態(tài)助動(dòng)詞體現(xiàn)。
主語是為小句命題的有效性負(fù)責(zé)的成分。只有明確了主語,英語小句對(duì)命題進(jìn)行協(xié)商才有了立足點(diǎn)與“責(zé)任人”; 只有主語與限定成分相結(jié)合,英語小句才具有轉(zhuǎn)變語氣類型的潛勢(shì)。在編碼方式上,英語小句主語“通常由表達(dá)事件概念的小句及表達(dá)物( thing,包括人) 概念的名詞詞組填充”( 何偉、王敏辰 2019: 124) 。名詞詞組做主語,需經(jīng)過指稱化。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堅(jiān)持級(jí)階假說,認(rèn)為一個(gè)級(jí)階上的語法單位由下一級(jí)階的語法單位構(gòu)成。也就是說,小句由詞組/短語構(gòu)成,不能直接由詞構(gòu)成。一個(gè)名詞不直接與物這個(gè)概念建立聯(lián)系,需根據(jù)情境的變換確定其指向,如名詞 bird 進(jìn)入小句時(shí),要具體為類指 the bird、定指 the bird 或 birds、不定指 a bird 或 birds 等。沈家煊( 2016: 124) 指出,名詞與動(dòng)詞并非具有普遍性的初始概念,指稱與述謂才是語言的原始功能。Kita( 2003) 、Diessll( 2013) 從語言起源與演變角度指出,指稱是語言產(chǎn)生后最初始的功能。指稱的對(duì)象不僅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事件。當(dāng)表事件概念的小句做英語主語參與者時(shí),也要發(fā)生指稱化,更確切地說發(fā)生名物化,通常以非限定形式出現(xiàn),或是由 that 引導(dǎo)的限定小句來填充,that 小句后置時(shí),須前置形式主語 it。
綜合來看,英語中的動(dòng)詞和名詞可以說是小句的句法結(jié)構(gòu)基石,只有經(jīng)過限定化和指稱化,它們才具有會(huì)話潛勢(shì),才能進(jìn)入會(huì)話語境,才能在語義層表達(dá)“情形”和“事物”。其他語法單位,比如性質(zhì)詞組、數(shù)量詞組、介詞短語等,通過修飾“情形”“事物”進(jìn)入小句與語篇。
漢語也有類似的編碼方式,然而,目的與英語相反。英語是為了構(gòu)建進(jìn)入語篇語境的合法小句,而漢語是為了構(gòu)建獨(dú)立于語篇、脫離語境的小句,即完句。完句是“不必借助情景語境或上下文就能夠獨(dú)立存在的始發(fā)句”( 賀陽 1994: 28) 。一個(gè)漢語完句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一是句干,即包括過程與參與者成分的基本結(jié)構(gòu); 二是完句成分,即“除了句干之外不可或缺的成分”( 金廷恩 1999: 11) 。完句研究主要聚焦哪些成分屬于完句成分。盡管不同學(xué)者對(duì)此看法不盡一致,但基本上都認(rèn)為完句成分涉及語氣、時(shí)體、情態(tài)、數(shù)量、程度、指代等范疇。比如:
18) 鳥飛。→ 鳥飛了。( 張雪平《漢語成句問題研究述評(píng)》) ( 19) 孩子聰明。→ 這孩子真聰明。( 張雪平《漢語成句問題研究述評(píng)》) ( 20) 盛碗里魚。→ 盛碗里兩條魚。( 沈家煊《“有界”與“無界”》) 例( 18) 添加了表達(dá)時(shí)體范疇的“了”,例( 19) 添加了表達(dá)指代范疇的“這”和表達(dá)程度范疇的 “真”,例( 20) 添加了表達(dá)數(shù)量范疇的“兩條”。“了”“這”“真”“兩條”都屬于完句成分,添加后小句脫離語境而獨(dú)立成句。這與上文提到的英語動(dòng)詞限定化、名詞指稱化等情況類似。何偉、仲偉( 2017) 在區(qū)分限定與非限定范疇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漢語限定與非限定的界定均限于完句。也就是說,具體言語行為中的漢語小句,不需要像英語那樣使用顯性的限定范疇與指稱手段,其命題解讀依賴語篇語境。
漢語小句命題進(jìn)入語篇語境時(shí)不需要限定化與指稱化,就具有人際潛勢(shì),這是因?yàn)闈h語思維建立在言者體驗(yàn)式上。語言為人類所創(chuàng)造,不可避免地帶有人的主觀性( Benveniste 1971) 。英語中將小句命題與語境建立聯(lián)系的限定范疇,不論構(gòu)建的是時(shí)態(tài)意義還是情態(tài)意義,都是說話人以自身所處的時(shí)空或自身的主觀態(tài)度為基點(diǎn)來描述事件。與英語不同,漢語的這種主觀性體現(xiàn)在人作為主體直接融入到小句表達(dá)的事件中,賦予小句以語境,給予一種臨場(chǎng)性的體驗(yàn)。比如:
21) 風(fēng)刮得很緊,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樣在空中飛舞,沒有目的地四處飄落。 ( 巴金《家》) 例( 21) 是巴金小說《家》的開頭第一句。以寫作時(shí)間為參照,小句描述的事件發(fā)生在過去,在英語中由過去時(shí)態(tài)體現(xiàn)。然而,漢語中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是以一種體驗(yàn)方式將小句事件與“現(xiàn)在”建立聯(lián)系,即人進(jìn)入描述的事件中,進(jìn)行一種臨場(chǎng)性的體驗(yàn)。又如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的第一句“我的故事,從 1950 年 1 月 1 日講起”,表明整個(gè)故事發(fā)生在過去,語篇以寫作或閱讀的“現(xiàn)在時(shí)間”為參照,對(duì)所發(fā)生的系列事件應(yīng)表述為過去發(fā)生的情形。但漢語以體驗(yàn)式的臨場(chǎng)描寫,將作者與讀者帶入 1950 年那個(gè)“現(xiàn)在”語境中,之后描寫的場(chǎng)景就如電影鏡頭一樣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使“讀者始終處于臨場(chǎng)的感覺”( 張濟(jì)卿 1998: 25) 。以英語比附漢語,較為相似的是祈使句,如小句 Do it 中沒有主語與限定范疇,而且在不同的語篇中都是同樣的表達(dá)形式,但小句卻能建立起與語境的聯(lián)系,這是因?yàn)樾【浔旧硖N(yùn)含了一個(gè)對(duì)話式的語境,蘊(yùn)涵了一個(gè)聽者以及體驗(yàn)式的“現(xiàn)在”時(shí)間參照點(diǎn)。
如上所述,英語小句命題進(jìn)入會(huì)話語境的方式,不論是限定化還是指稱化,都有較明確的體現(xiàn)形式。漢語構(gòu)建了一種臨場(chǎng)性的體驗(yàn),小句命題不需要顯性的限定范疇與指稱手段,本身已經(jīng)融入語境,具有人際潛勢(shì)。因此,漢語小句命題的邏輯運(yùn)行方式與英語不同,各句法成分在形式上的區(qū)分不明顯,界限比較模糊。如名詞可以做主語,也可做謂體; 動(dòng)詞做主語與做謂體時(shí),并沒有限定化或非限定化的區(qū)分。
五、英漢主述位結(jié)構(gòu)及編碼方式
語篇功能關(guān)注如何運(yùn)用語言組織信息,表明信息之間以及信息與語境之間的關(guān)系。語言的組篇功能主要由互文方式、主述位結(jié)構(gòu)、信息結(jié)構(gòu)和銜接手段體現(xiàn)( 何偉、郭笑甜 2020: 43) 。本文主要以主述位結(jié)構(gòu)為切入點(diǎn),兼以其他語篇組構(gòu)手段,對(duì)比英漢語語篇功能的編碼方式。比如:
( 22) You probably haven't heard of the SOU before. That's because we fight cruelty undercover. (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 23) 營(yíng)業(yè)員手一扳,轉(zhuǎn)過柜臺(tái),竹殼熱水瓶擺到紹興酒壇旁邊,漏斗插進(jìn)瓶口,竹制酒吊,陰篤篤,濕淋淋提上來,一股香氣,朝漏斗口一橫,算半斤。( 金宇澄《繁花》) 例( 22) 中,兩個(gè)小句的主位分別為 You 與 That,剩余部分為述位。That 作為第二個(gè)小句信息的起點(diǎn),指代前面整個(gè)小句的內(nèi)容,在信息結(jié)構(gòu)中是已知信息,后續(xù)為新信息。從銜接角度, That 是一種指稱手段,指代前面整個(gè)小句。
漢語語篇中常見流水句,流水句一般由多個(gè)句式不同的小句組成。如例( 23) 共有十個(gè)小句,每個(gè)小句都由逗號(hào)隔開,除了第一個(gè)、第三個(gè)和第四個(gè)為主謂齊全小句外,其余皆為非主謂結(jié)構(gòu)小句或主謂結(jié)構(gòu)不齊全小句。對(duì)于主謂結(jié)構(gòu)完整的小句,可以比較容易地明確其主位,如這幾個(gè)小句中,“營(yíng)業(yè)員”“竹殼熱水瓶”“漏斗”分別做小句的主位。而對(duì)于主謂結(jié)構(gòu)不完整的小句,主位識(shí)別呈現(xiàn)出不同的難易程度。有明確謂體的小句易于確認(rèn)省略成分,如可認(rèn)為小句“轉(zhuǎn)過柜臺(tái)”省略了主語“營(yíng)業(yè)員”,小句“陰篤篤”和“濕淋淋提上來”都省略了主語“竹制酒吊”,這些省略了的主語都可視為小句的主位。對(duì)于在體現(xiàn)形式上只有名詞詞組的小句則難于確定其主位與述位,如小句“竹制酒吊”“一股香氣”。在分析及物性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時(shí),上文指出不能依據(jù)英語的形式邏輯簡(jiǎn)單地以“省略”一言蔽之,因?yàn)槭÷缘男问讲⒎侵挥幸环N。這樣一來,這類漢語小句的主述位結(jié)構(gòu)劃分也就有了不確定性。
從結(jié)構(gòu)上,漢語中這種主謂不完整小句被稱為零句,零句是根本,具有獨(dú)立性( 趙元任 1968,1979: 51) 。同時(shí),趙元任( 1968,1979: 42) 也明確指出,零句常見于對(duì)話或伴隨具體行動(dòng)的場(chǎng)景,即零句獨(dú)立性在于強(qiáng)語境性。因此,對(duì)于零化較為突出的小句,如“竹制酒吊”“一股香氣”等僅有名詞詞組的小句,對(duì)其進(jìn)行語法分析必須注重上下文或更大的語境。“竹制酒吊”的上文為“竹殼熱水瓶擺到紹興酒壇旁邊,漏斗插進(jìn)瓶口”,結(jié)構(gòu)上呈現(xiàn)對(duì)仗格式,“竹制酒吊”與此并置在一起,從結(jié)構(gòu)平衡上來說,應(yīng)該屬于同種格式,隱含了“竹制酒吊掛在酒壇中” 這一關(guān)系過程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因?yàn)閷?duì)仗本身提供了一個(gè)結(jié)構(gòu)上相互識(shí)解的語境。如“茶喝”單獨(dú)不能說,但在對(duì)仗格式“飯吃”“茶喝”“煙抽”中卻能成立( 儲(chǔ)澤祥、王艷 2016: 326) 。“竹制酒吊”的下文為“陰篤篤,濕淋淋提上來”,可以說,這兩個(gè)小句的隱性主語為“竹制酒吊”。那么,也正是這種上下文語境,促成了“竹制酒吊”以零化方式獨(dú)立存在。從更大的上下文語境可以看出,小句“竹制酒吊”為后續(xù)小句提供背景信息,可視為主位,方琰( 2019: 18) 將此類小句視為語境主位,因?yàn)樗鼮楹罄m(xù)小句建構(gòu)語境。同時(shí)也不應(yīng)忽視與上文的關(guān)系,對(duì)于上文而言,小句“竹制酒吊”發(fā)展了前面小句中的述位。從信息結(jié)構(gòu)上,對(duì)于上文它是新信息,而對(duì)于下文又是舊信息。從修辭的角度,它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樣,對(duì)于小句“一股香氣”,我們也可做類似的分析。
綜上,英語小句的概念功能與人際功能有較明確的語法化編碼形式,每個(gè)小句的句法結(jié)構(gòu)具有完整性,因此主述位結(jié)構(gòu)的劃分也具有明確性。漢語主述位結(jié)構(gòu)劃分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漢語本質(zhì)上是一種臨境性語言,對(duì)主述位的分析需要超越詞匯 語法層,深入到語義層與語境層,具體識(shí)別上需要擴(kuò)展到上下文,甚至更大的語境。
六、英漢語本質(zhì)差異
如上所述,從三大元功能角度來看,英語有較高的語法化程度,如概念功能中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的完整性與嚴(yán)謹(jǐn)性、邏輯關(guān)聯(lián)詞的突顯性,人際功能中語氣結(jié)構(gòu)的限定化與指稱化,語篇功能中主述位結(jié)構(gòu)的明晰化。漢語的語法化程度較低,如及物性語義配置結(jié)構(gòu)比較松散,有些結(jié)構(gòu)具有模糊性,對(duì)應(yīng)的主述位結(jié)構(gòu)也不具完整性,常常難以劃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漢語小句有時(shí)不像英語那樣需要完整的語氣結(jié)構(gòu)。這表明,漢語并非遵循英語一樣的形式邏輯,而是“簡(jiǎn)單明了,從不多余,讓聽者自己得到答案”( 沈家煊 2014: 1) 。兩種語言在三大元功能編碼方式上的差異可借鑒人類學(xué)家 Hall( 1976) 對(duì)世界文化類型的描述而范疇化為“弱語境型語言”( low-context language) 與“強(qiáng)語境型語言”( high-context language) 的對(duì)立。在 Hall( 1976: 90) 看來,一個(gè)事件可從三個(gè)方面來看,即代碼、語境和意義,對(duì)一個(gè)事件正確的認(rèn)識(shí)( 即對(duì)其意義的識(shí)解) 需要看文化的類型。Hall( 1976: 91) 認(rèn)為世界上的文化可區(qū)分為弱語境文化和強(qiáng)語境文化。在編碼和解碼事件的意義時(shí),弱語境文化強(qiáng)調(diào)“言傳”,主要通過明晰的語言來傳遞信息,語境的作用較小; 強(qiáng)語境文化強(qiáng)調(diào)“意會(huì)”,使用語言傳達(dá)的信息相對(duì)較少,語境的作用較強(qiáng)。
英漢語的編碼方式表現(xiàn)出對(duì)語境依賴程度的不同,這種語言類型上的本質(zhì)差異應(yīng)歸于西方與中國(guó)哲學(xué)基本思維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學(xué)思維注重本體追問,主張主客二分。從泰勒斯提出的水本源說開始,再到亞里士多德提出什么是存在的存在,西方哲學(xué)思維形成了一種追問世界本體存在的傾向,而且將這種追問建立在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嬌稀N鞣降倪壿嫿⒃谡Z言之上,語言這個(gè)詞“在希臘語叫 logos,后來發(fā)展出了邏輯這個(gè)詞,建立起邏輯學(xué)科”( 鄧曉芒 2007: 141) ,“主謂結(jié)構(gòu)是西方語言和語法的主干,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石”( 沈家煊 2018: 2) 。英語中主謂結(jié)構(gòu)之所以重要,是因?yàn)檫@一語法構(gòu)造蘊(yùn)含了西方的邏輯。主語是英語小句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為小句的互動(dòng)行為承擔(dān)責(zé)任”( Halliday 1994: 76) ,只能由名詞詞組或名物化成分填充,因?yàn)橹挥形? thing) 才是實(shí)在的存在,才能承擔(dān)責(zé)任。而這個(gè)實(shí)在源于一個(gè)本體,即存在的存在,如 the bird、a bird 和 birds 等都有一個(gè)更為抽象的 bird。謂體描述了存在的狀態(tài)、運(yùn)動(dòng)及關(guān)系等,謂體的體現(xiàn)形式是動(dòng)詞。動(dòng)詞通常表達(dá)的是一種動(dòng)作行為,動(dòng)作行為只能在時(shí)間中展開,因此英語動(dòng)詞攜帶了時(shí)標(biāo)記才能進(jìn)入語境。和名詞一樣,動(dòng)詞也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更抽象的本體的存在,語境中攜帶不同時(shí)態(tài)的動(dòng)詞只是這個(gè)本體在具體使用中的反映。同時(shí),英語主謂結(jié)構(gòu)與命題結(jié)構(gòu)緊密關(guān)聯(lián),可以說是一種同構(gòu)關(guān)系,主語表達(dá)了“是什么”,謂體表達(dá)了“怎么樣”。英語語法邏輯上表現(xiàn)出清晰的主謂結(jié)構(gòu),主語與謂體在形式與功能上的明確區(qū)分,反映和構(gòu)建了西方哲學(xué)對(duì)本體追問的精神本質(zhì),是哲學(xué)中本體概念發(fā)達(dá)的體現(xiàn)。“對(duì)西方人來說, to be 還是 not to be,這是個(gè)首要問題”( 沈家煊 2020: 4) 。換言之,這種追問由語言構(gòu)造體現(xiàn),也是語言構(gòu)造所造成的。進(jìn)一步講,西方哲學(xué)思維對(duì)本體的重視意味著主體和客體的分離,正如潘文國(guó)( 1997: 364) 所說,西方哲學(xué)注重“保持物我之間的距離,只有隔開了距離,才能對(duì)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冷靜的剖析”。相應(yīng)地,在語言編碼中,英語小句對(duì)主體、客體功能角色的體現(xiàn)也就比較清晰,對(duì)相關(guān)動(dòng)作或狀態(tài)的時(shí)間指示性表達(dá)也就有明確的要求。
中國(guó)哲學(xué)主張?zhí)烊撕弦唬⒅刂骺鸵惑w。天與人不是對(duì)立的兩個(gè)范疇,而是人為天,天也是人,天與人是一生二的關(guān)系。天人合一這種哲學(xué)觀使得我們?cè)谔綄な澜绫举|(zhì)過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認(rèn)知取向。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對(duì)世界本源解釋最為深刻的是老子提出的“道”,至于“道”是什么,則是“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可說的。儒家提出的社會(huì)倫理體系,也是一種“道”,是“道”的具化,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種“道”,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guān)系是自然,這種自然關(guān)系可以衍推到君臣關(guān)系等。如果說,這是“道”在社會(huì)層面的體現(xiàn),則可知其本質(zhì)是自然,“道法自然”。“自然的原則是道家哲學(xué)的原點(diǎn),也是中國(guó)文化的原點(diǎn)”( 鄧曉芒 2015: 207) 。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世界的本源就是如此,是不可說,不必說的。也就是說,本源自然存在,不必追問。同時(shí),中國(guó)哲學(xué)又歷來關(guān)注人的主體性,儒、釋、道從根本上都強(qiáng)調(diào)人的參與性( 潘文國(guó) 1997: 363) 。也就是說,中國(guó)哲學(xué)主張?zhí)烊撕弦弧⒅骺鸵惑w,把主體看作客體的一部分,但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人的主導(dǎo)性。這種思維傾向不易形成表達(dá)清晰的范疇,對(duì)世界經(jīng)驗(yàn)的認(rèn)識(shí)及表達(dá)比較依賴人的主體性和自覺性。由此,漢語語法構(gòu)建方式不同于英語。漢語中各語法單位、語法成分之間不像英語那樣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漢語的名詞沒有所謂的本源形式,如“鳥”一詞,可以直接入句,沒有必要像英語一樣加上定冠詞等; 漢語的動(dòng)詞在入句時(shí)一般也不需要明確的時(shí)體標(biāo)記; 漢語小句對(duì)主體、客體功能角色的體現(xiàn)比較模糊,有時(shí)很難區(qū)分哪個(gè)成分是主體,哪個(gè)成分是客體,甚至有時(shí)亦主亦客; 漢語中的省略可以是任何成分; 漢語小句的表達(dá)可以不符合形式邏輯。這些都是漢語的一種常態(tài),在交流中一般不會(huì)引起誤解,這是因?yàn)樵捳Z雙方在編碼與解碼中都有很強(qiáng)的臨境意識(shí)。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英語思維上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漢語主張?zhí)烊撕弦弧⒅骺鸵惑w,只是指兩種思維中有這樣的傾向性,不是絕對(duì)的。英語注重區(qū)分主客體,語言有更多的形式范疇。漢語強(qiáng)調(diào)主客一體,語言中較少形式邏輯范疇,強(qiáng)調(diào)語境參照理解。
七、結(jié) 語
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認(rèn)為,元功能思想具有理論普適性,任何自然語言都具有三大元功能,然而不同語言的編碼方式確有不同。本文對(duì)比了英漢兩種語言的及物性結(jié)構(gòu)、邏輯 語義連結(jié)、語氣結(jié)構(gòu)以及主述位結(jié)構(gòu),發(fā)現(xiàn)兩種語言在元功能的編碼方式上存在差異: 英語為弱語境型語言; 漢語為強(qiáng)語境型語言。通過闡釋,本文認(rèn)為英漢語言類型上的差異源于哲學(xué)基本思維方式上的不同: 英語注重本體追問、主客二分,從而語言中的形式范疇多,即重“言傳”,言豐意簡(jiǎn); 漢語主張?zhí)烊撕弦弧⒅骺鸵惑w,從而語言中的形式范疇少,即重“意會(huì)”,言簡(jiǎn)意豐。總之,“弱語境”與“強(qiáng)語境”、“本體追問”與“天人合一”或“主客二分”與“主客一體”等對(duì)立范疇?wèi)?yīng)是英漢之間在語言、哲學(xué)思維兩個(gè)層面上的本質(zhì)差異所在。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